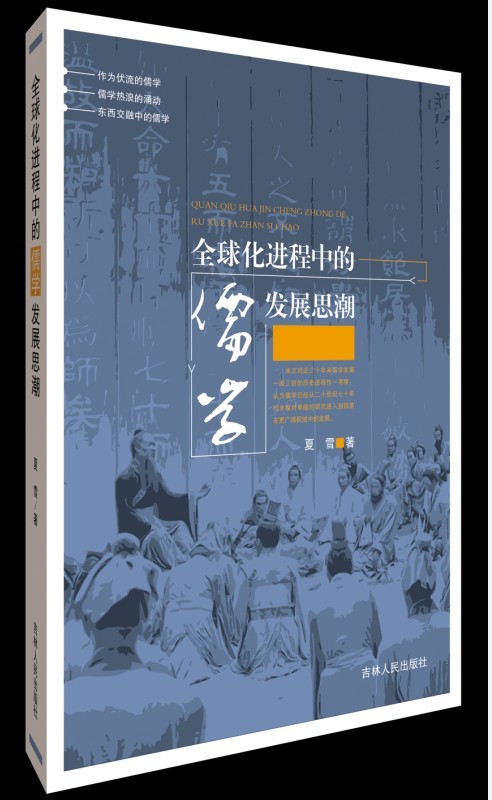
《全球化進程中的儒學發展思潮》引論
二十一世紀全球文化發展趨勢仍舊是極為復雜的問題。全球化、國際化將給我們帶來新的挑戰,全球化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加劇了對世界發展中國家不同文化的差異性和根源性的“同質化”,民族文化日益被放于跨民族的文化網絡之中,導致其民族性的日益淡化,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沖突,甚至會造成文化的消亡。
若說到中國的“本土文化”,“儒學”無疑是躍出的第一個詞。雖然,中國傳統文化包括了多個部分,并各自有其特點。對此,牟宗三曾說:“察業識莫若佛,觀事變莫若道,而知性盡性,開價值之源,樹價值之主體,莫若儒。”[1]湯一介曾說:“如果沒有儒家,那么中國文化傳統就可能中斷;如果沒有法家,那么中國文化就不可能突破;如果沒有道家,中國文化就不可能那么豐富多彩,富有啟發性。”[2]但是,他們的言論中也凸顯了對儒學的重視,認為儒學是中國傳統價值觀形成的源泉和樹立的主體,是中國文化悠長的保證。因此,中國傳統文化雖不拘限于儒家,但是“中國傳統思想,以儒家為主干”。[3]錢穆曾說:“儒家思想為中國文化之骨干,此義人人知之。蓋儒學本于中國文化而孕茁,自有儒學而中國文化亦遂發揚光昌而滋大。儒學本于孔子,然孔子曰:我好古敏以求之。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孟子稱之曰:孔子之為集大成。故雖謂儒學為中國古代文化之結晶可也。”[4]牟宗三認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內容是以儒家為主流所決定的一個文化方向、文化形態”。[5]《新不列顛百科全書》更是對“儒學”做了如此解釋:“儒學作為中國人所遵循的生活之道的表征已大大超過兩千年。由于它奠基于孔子(公元前551-479),所以在中國,儒學一詞已經是知識的同義語,并且被一些人把它看成一種宗教。儒學的影響竟如此之大,以至于不論是誰,只要被請來用一個詞概括傳統的中國生活和中國文化的話,這個詞將會是‘儒家的東西’。”[6]儒學“一直對中華文化各個層面產生著巨大而又深遠的影響。儒學統攝宗教、哲學、倫理、政治、教育、藝術等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品格及關懷現世人生的精神,使它成為一套全面安排人間秩序的思想體系,從一個人的生存方式,到家、國、天下的構成,都在儒學關懷與實踐的范圍之內。經過二千多年的傳播、積淀,儒學一直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心理結構的形成”,[7]儒家追求的“內圣外王之道”一直是中國人的人格修養和經世事業的價值理想。基于此點認識,本文所講的“中國傳統文化”即以儒學展開論述。
儒家文化將不可避免地隨同全球化的趨勢參與世界文化的行列,并與世界各種文化進行全方位的交流、對話與競爭。儒學在傳統向現代的進程中是否已經找到屬于它自己的話語空間?它能否在二十一世紀參與世界文化的構建?它將以何種面貌應對二十一世紀文化的挑戰?等等,都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要回應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從上個世紀的儒學發展演變中獲得啟示。百年來,儒學經歷了解體、重構與融構,通過“西學中源”、“中學西源”、“中體西用”、“西體中用”、以“西學”釋“中學”、“中西會通”、“全盤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接續主義”、“本位文化”、“創造性轉化”、“合題”、“解體與重構”、“和合”等各種方式對自身進行調適,以期緊隨時代的步伐。而這一過程遠未結束。許多杰出的知識分子參與并引領著潮流,誠如高力克所說,中國現代化運動是以先進知識分子對現代化問題的認知、選擇和規劃為基底的[8]。他們致力于弘揚中國文化,且卓有所成;他們以其良好的中西方文化素養、積極客觀的心態和高瞻遠矚的視野,在全球化與本土化共同發展的背景下探索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他們體認、批判、發掘儒學的價值,并作創造性的現代詮釋,力圖融合中西、加速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推動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而現代化是一個尚在持續的變遷過程,基于此背景的文化詮釋必然也有其追尋和被追尋的意義。一般來說,以史學史和學術史方法,將一些旨趣相類的學者做一系統性排比研究,通過縱向比較,可以發現某一思潮的傳承與發展;通過橫向比較,可以發現社會思潮在某一歷史時段的多種表現形式。尤其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文化現代化是極其重要的一個方面。而中國文化的更新、重構與升華,離不開對“千年傳統”和“百年傳統”的開采與發掘,[9]離不開知識分子對文化的詮釋與發展。我們注重研究文化,并深刻領會文化在我國乃至東亞現代化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從其歷史的演變中尋求一些規律供現實借鑒,是具有社會現實意義與學術理論意義的。
首先,雖然有學者聲稱儒學已經“博物館化”,其生命已經終結[10],但通觀20世紀中國思想史,可以發現,儒學仍在憂患中卓然挺立,回應西方文化和現代化的挑戰,并形成了幾次高潮。而之所以選取“近三十年”為縱向時間斷限,是因為我們認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尊孔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盲目反孔的時代也已經過去了。時代在前進,學者們也放開胸懷,針對儒學的眾多方面展開了研究,一時間百家爭鳴,展現了一段時期的學術繁榮。
最近三十年中,儒學的經歷可謂一波三折。1978年左右,出現了重新評價孔子和儒學的思潮,儒學逐漸走出被完全否定批判的境地,得到較為公正全面的研究和評價。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在自由主義、啟蒙主義、全盤西化等思潮涌動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儒學并非顯學,基本上,當時的學術界是把批判中國文化傳統、引進西方思想作為主題,儒學仍舊是被認為是中國現代化的阻礙力量而居于被批判的地位的。所以,杜維明當時在中國提倡討論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可能性是比較“另類”的聲音[11]。九十年代,當用來解決社會問題的種種理論、主張和措施不能達到預期效果,越來越多的人把目光轉向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希望從中尋找到新的思想文化資源。傳統文化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并形成了尋找和弘揚傳統文化、傳統道德的“國學熱”。但是,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使儒學對于現代化的作用受到質疑,它被從頂端拋落下來。2004年在中國大陸興起的“讀經熱”則將又其推上風頭浪尖,不得不接受人們評頭論足。
其次,這一時期有許多學者認同“儒學要繼續存在,必須要更新轉化”的觀點,他們所做的是更具有現實實踐意義的工作,即探索“儒學應該怎樣進行更新轉化”和“儒學應該進行怎樣的更新轉化”的問題,如張岱年探討融合中西、貫通古今的“文化綜合創新”;杜維明探討“儒學的第三期發展”;余英時探討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的契合;金耀基探討儒家倫理與香港社會經濟的關系;王家驊通過中日儒學比較研究探討儒學在當代中國如何存在的問題;張立文提出“和合學”欲使儒學加入全球文化對話;黃俊杰等人致力于“東亞儒學詮釋學”的建構,從方法論探討儒學的現代存在方式等。同時,這一時期的文化熱點問題如讀經運動引起的有關爭論、東亞金融危機引起的對儒學的反思等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使得儒學現代化問題在東亞乃至世界得到廣泛關注。我們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學者研究儒學,已經不僅僅將它放置在中國這一環境中,而是擴大到東亞、世界的視域,探討其在全球化語境下的生存。
另外,中國知識人的特點是具有“憂患情懷”,具有“參與意識”,儒學“命脈”的延續,即得益于眾多知識分子的不懈努力。針對儒學,他們有的側重于“破”,有的側重于“立”。我們主要關注這樣一類學者,他們熱愛中國歷史文化,念念不忘民族文化復興,力圖以儒家思想為主體,吸收、融合、改造西方近現代的思想和文化,尋找使傳統中國通向現代化的較平穩的道路。我們欲著重研究他們如何認識傳統文化,并對傳統文化進行新詮釋;如何認識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關系;如何促使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和諧發展。
由此,我們梳理了近三十年儒學發展思潮,我們也發現,傳統儒學已經在更新,中國傳統文化已開始其“融構”的過程。儒學的更新意味著精神現代化的進行,而精神層面的現代化被認為是現代化三圈層中最艱難的一環,它要經歷一個長期而艱難的過程。所謂“前事不忘,后事之師”,那么,讓我們回顧一下它過去二十多年間的經歷吧。
[1] 牟宗三:《生命的學問》,臺北:三民書局1970年版。
[2] 湯一介:《論文化轉型時期的文化合力》,《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湯一介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 《中國傳統思想中幾項共通的特點》,錢穆:《新亞遺鐸》,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191頁。
[4] 錢穆:《中國近代儒學之趨勢》,《思想與時代》1944年4月第33期,第11頁。
[5] 牟宗三:《從儒家當前使命說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牟宗三先生全集》1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年版。
[6] 楊煥英主編:《孔子思想在國外的傳播與影響》,教育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79頁。
[7] 傅永聚、韓鐘文:《現代新儒學研究·前言》,傅永聚、韓鐘文主編:《二十世紀儒學研究大系》,中華書局版。
[8] 高力克:《歷史與價值——中國現代化思想史論》,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9] 關于“千年優秀傳統”、“百年優秀傳統”的描述見盛邦和:《解體與重構——現代中國史學與儒學思想變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頁。
[10] [美]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鄭大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11] 杜維明:《一陽來復》,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4頁。
序:一部“東亞學”研究的力作
盛邦和
夏雪的著作《全球化進程中的儒家思潮》即將正式出版。日前她要我寫幾句話,放在書前。
1996年期間,我繼續前往日本東京大學國際關系論研究室從事東亞文化研究,不久,接到母校華東師范大學的通知,任命我為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專業博士生導師,并為此博士點負責人。回國后招生授業,夏雪成為我指導的博士生中的一員。記得當時給學生們確定研究方向,用了三個主題詞表達:東亞、文化、現代化。“東亞”,是地域東亞,又是文化東亞。將東亞三國,即中、日、韓確定為考察平臺,開展文化與現代化比較研究,成為我們的志向。我的博士論文是《黃遵憲史學研究》,涉及黃遵憲的《日本國志》,算是“東亞”研究的開啟吧。以后又刊《內核與外緣——中日文化論》、《透視日本人》,主編《東亞學研究》叢書,求此研究的深入。關注史學與儒學成為東亞學的特點,故有《東亞:走向近代的精神歷程——近三百年中日史學與儒學傳統》、《解體與重構:現代中國史學與儒學思想變遷》的出版。最近新出《亞洲與東方學研究——東亞文明的進化》一書,還是緊咬“東亞”不放,焦點還在東亞儒學。華東師大曾先后設立“日本研究中心”與“東亞文化研究中心”。圍繞“中心”從事研究的日子,成為我和我的博士生學術生涯中的一個重要階段。
我們認為,一個民族與地域的文化,要生存與進步,須與世界交流與融合。與世隔絕、抵御交融,結果是停滯與退化。一坨生鐵跌入水中與一勺鮮奶傾入水中,結果迥異。前者隔絕,后者交融。東亞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具有現實功用性及包容性的突出表現。日、韓現代化的過程說明了這一點。設想世界上由諸多文化圈組成,如基督教文化圈、佛教文化圈等。每個文化圈都有其內核文化與外緣文化的區別。內核文化是源地文化、原典文化、古老文化,由此也是抵御性最大,遺傳性最強的文化。一方面,世界上每個國家都必須融入世界,江流入海,不可阻擋。一方面又要看到,承受“內核”重負的中國,視其文化更新的歷程,恰如荷重登山,步步艱難。百年中國的發展,因遭遇更多的周折與險阻,而顯分外的遲緩與艱難。直至今天都難說古老儒家已真正完成與“現代”的“對接”。由此,為求文化的進步與昌明,當決心更堅,給力更大,倒退沒有出路。
可以說一千遍傳承儒家的話,如果不在“更新”上注力,儒家文化終將無法適應文明進步而消亡。舊儒家因蔑視“奇技淫巧”而懷疑科學,因主張“三綱五常”而反對民主,因溺于蒙昧而妨礙國民性提升。因此才有“五四”批儒運動的風起云涌,才有“民主、科學”口號的震聾發聵。必須看到日本近代以來,融新儒學而造明治新文化。反之突出“儒教”老觀念,踏上“攘夷”舊途徑,結果隔絕世界,拒絕文明,步入專制尚武的時代。一切明治成果亦化為泡影。在中國,中體西用思想的推出及袁世凱的“崇儒”設教,表現出抵制世界潮流,回歸復舊道路的亢奮神態。一旦“現代”走入瓶頸,舊文化常披上宗教的外衣,以其根深蒂固的影響,引車倒退。所幸中國儒學為“學”,而非宗教。回顧中國新文化運動,作今日理性的思考,其運作發端的初衷,實在于通過思想震蕩,以求中國文化包括儒家的復興再造。中國舊傳統的地基很深沉,中國老文化的傳統很悠長。少不了這樣的暴風驟雨,少不了這樣的“矯枉過正”。但是,如果只是推陳而忘卻出新,只是“破”而淡漠“立”,新文化建設的任務無法完成。肯定地說,文化中國必將立出科學的儒家、民主的儒家、支持市場經濟的儒家。總之是具備現代精神的儒家。馬克斯·韋伯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其中道理啟迪世間。這是說,現代化需得到文化的支持。當民族文化陳舊未變,現代化將因舊文化的阻滯而停滯。
夏雪的著作,論述東亞與中國儒家文化的特質,關切中國在東亞文化圈的地位,
是化并注意到韋伯理論。指出,歷史變革促使舊文化通過“現代”詮釋,而生新意義。所謂詮釋,首先是“解讀”原著,確認文化更新的原典本色。然后是“解體”舊義,對傳統文化中有違“現代”的內容,作“解散”式分析批判。繼而是“重構”新學,融入嶄新的現代意義,對傳統元素作新構建。經解讀、解體、重構,舊儒家有可能成為新儒家。儒家是巨大的礦藏,熔化沉滓,顯現精華。禮義廉恥、忠孝節義、仁義禮智信,這一系列道德元素,依然熠熠閃光,于今有用。原始的叢林文明、古代的土地文明與現代的市場文明,是文明進化的三個歷程。前兩個文明為舊文明,而后的文明為新文明。儒家更新就是將生于舊文明的舊儒家改造為適應新文明的新儒家。“適者生存”,完成這個更新,方可推陳出新、浴火求生。
因此,本書當為一部“東亞學”研究的力作。其中提出的不少問題,益智啟思,有利于中國文化建設。望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序二:文化中華與全球化
孟凡東
20世紀末21世紀初,世界正經歷著大變化,全球化成為這一時期的重要特征。有人認為全球化僅僅是經濟全球化,有人認為全球化是全方位的,也包括文化全球化。細細考察世界各個民族文化的變化,探究其變化樣態,可以研究全球化與世界各文化之間的關系,全球化與區域化的關系。因此,文化全球化不能簡單等同于經濟全球化。21世紀全球文化發展趨勢仍舊是一個極為復雜的問題。人們更多地關注:全球化、國際化將給世界帶來新的挑戰,全球化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加劇了對世界發展中國家不同文化的差異性和根源性的“同質化”,民族文化日益被置于跨民族的文化網絡之中,導致其民族性的日益淡化,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沖突,甚至會造成文化的消亡。與此同時,世界各文化也在經歷著調適與變革。
儒家文化在20世紀經歷了巨大的變革。這種變革不僅僅是其內在的變化,而且也是幾代學者的努力。在全球化進程中,儒家文化也在被“自覺”。儒家文化將不可避免地隨同全球化的趨勢參與世界文化的行列,并與世界各個文化進行全方位的交流、對話與競爭。儒學在傳統向現代的進程中是否已經找到屬于它自己的話語空間?它能否在二十一世紀參與世界文化的構建?它將以何種面貌應對二十一世紀文化全球化的挑戰?等等,都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要回應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從20世紀的儒學發展演變中獲得啟示。百年來,儒學經歷了解體、重構與融構,通過“西學中源”、“中學西源”、“中體西用”、“西體中用”、以“西學”釋“中學”、“中西會通”、“全盤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接續主義”、“本位文化”、“創造性轉化”、“合題”、“解體與重構”、“和合”等各種方式對自身進行調適,以期緊隨時代的步伐。儒家文化和東亞文化在不斷更新中,文化傳統在持續再造中,而這一過程遠未結束。
20世紀下半葉,東亞模式的飛速發展,帶來了世界的關注;21世紀初,世界變革中的東亞,更為世人矚目。此間,中國文化自覺也塑造著中國的文化變革、更新。夏雪的著作反映了這一現實的變化。要討論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與中國人的文化自覺與社會發展問題,應該澄清有關對儒學的誤解與非難,要對儒學有起碼的體認,從而詮釋、借鑒、更新儒家文化的資源。對這樣一群知識分子的研究既反映出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歷程,也反映出中國歷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深層課題。從近30年的儒學變遷入手,深刻領會文化在中國乃至東亞現代化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從其歷史的演變中尋求一些規律供現實借鑒,其社會現實意義與學術理論意義是非常明顯的。
首先,夏雪認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陸的儒學研究發生了不同于此前十年的轉變。1978年左右,出現了重新評價孔子和儒學的思潮,儒學逐漸走出被完全否定批判的境地,得到較為公正全面的研究和評價。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在自由主義、啟蒙主義、全盤西化等思潮涌動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儒學并非顯學,基本上,當時的學術界是把批判中國文化傳統、引進西方思想作為主題,儒學仍舊是被認為是中國現代化的阻礙力量而居于被批判的地位的。20世紀九十年代,當用來解決社會問題的種種理論、主張和措施不能達到預期效果,越來越多的人把目光轉向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希望從中尋找到新的思想文化資源。傳統文化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并形成了尋找和弘揚傳統文化、傳統道德的“國學熱”。但是,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使儒學對于現代化的作用受到質疑,它被從頂端拋落下來。2004年在中國大陸興起的“讀經熱”則將又其推上風頭浪尖,不得不接受人們評頭論足。因此,“伏流中的儒學”重點考察了這一變化。儒學被解體,被否定,被肯定。學者們認為應該從保存人類文化遺產的高度來認識孔子思想的存廢問題,認為對于一切以往思想文化知識的繼承,都必須經過認真的探討、批判和改造,才能達到“古為今用”的目的。
其次,這一時期有許多學者認同“儒學要繼續存在,必須要更新轉化”的觀點,他們所做的是更具有現實實踐意義的工作,即探索“儒學應該怎樣進行更新轉化”和“儒學應該進行怎樣的更新轉化”的問題,如張岱年探討融合中西、貫通古今的“文化綜合創新”;杜維明探討“儒學的第三期發展”;余英時探討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的契合;金耀基探討儒家倫理與香港社會經濟的關系;王家驊通過中日儒學比較研究探討儒學在當代中國如何存在的問題;張立文提出“和合學”欲使儒學加入全球文化對話;黃俊杰等人致力于“東亞儒學詮釋學”的建構,從方法論探討儒學的現代存在方式等。同時,這一時期的文化熱點問題如讀經運動引起的有關爭論、東亞金融危機引起的對儒學的反思等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使得儒學現代化問題在東亞乃至世界得到廣泛關注。這一時期,學者研究儒學,已經不僅僅將它放置在中國這一環境中,而是擴大到東亞、世界的視域,探討其在全球化語境下的生存。
再次,文化是探索世界范圍的現代化發展、全球化發展的重要變量。有觀點認為,“如果不承認并探求那些靈巧使用的科技器材背后的文化及文明力量,不承認并探求那些把人類帶入一個巨大、艱難而帶有挑戰性的時代轉變背后的神話,那將是悲劇性的錯誤”。二十世紀后半葉,東亞地區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舉世矚目。有人甚至認為,東亞在西歐之后,產生了“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第二個個案”。東亞在現代化上的成功引發了學者對“現代化”、“現代性”的新思考。這一討論也堅定了學者對文化價值的認同。熱浪涌動的“儒學”正經歷著更新:“重構”與“再造”。儒學的現代功用是文化建設的合理路徑。
最后,中國知識人的特點是具有“憂患情懷”,具有“參與意識”,儒學“命脈”的延續,即得益于眾多知識分子的不懈努力。針對儒學,他們有的側重于“破”,有的側重于“立”。
一般人認為,對于文化研究還非常不成體系,沒有形成一個共識。文化研究讓人摸不到頭緒,無從談起,也不能亂談。
“文化轉型”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精神革命”型,這一類社會以西方文化變革為代表,經歷了“宗教革命”,俗世化帶來了西方社會質的變化,同時結合其他科學革命、政治革命與產業革命而完成了西方“內發型”現代化;第二類是“精神改革”,這一類社會以東亞文化變革為代表,沒有經歷“宗教革命”,傳統精神文化是經歷了西方的沖擊,出現了創造性的回應,經過文化更新,才產生了“新精神文化”,因此,不是西方革命意義的文化轉型,但是不能說東亞社會就沒有變化。東亞社會的傳統也在經歷現代轉化,從東亞社會整體發展來看,這一變化還是相當漫長的。
文化現代化原本就是整個現代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它與政治經濟現代化有著相互“發明”、相互推動、相互制約的關系。作為一個現代化后進的中國,文化現代化對政治經濟現代化的支持和制約的關系更加分明。更何況,沒有文化現代化的現代化談不上完成了現代化,這樣的現代化也不是宜居的現代化,在現實中是不可能長期存在的,甚至根本就不會存在。從中國現代化進程來看,中國社會也必須經歷“文化轉型”,核心內容是現代性的工商精神倫理體系的建立,探究文化更新后的“新中華文化”對中國全面現代化發展產生巨大的精神文化層面支持作用或積極歷史意義。傳統文化不經歷文化更新、創造性回應,不融合其他文化,不能形成“文化傳統”,就不能產生“新中華文化”。是為“文化中華”建設。
希冀“再造”的“儒家新文化”為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中國現代化提供“滋養”。
于北大燕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