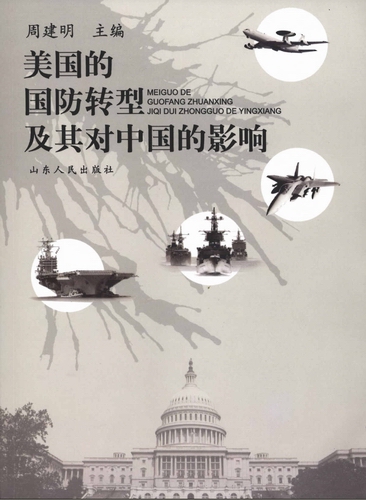
由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周建明主編的《美國的國防轉型及其對中國的影響》一書已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為國家社科基金資助的課題成果,共計14章30余萬字,從陸軍、海軍、空軍、海軍陸戰隊和太空軍事力量,到核戰略、本土安全戰略、情報與后勤、信息網絡、盟國關系、科技支持等方面,全面介紹了正在進行中的美國國防轉型及其對中國的含義,為中國的國際關系學者、特別是美國戰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本難得的教材。
序 言
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臺以來,美國迅速實施了國家安全戰略的轉型。9·11事件之后,美國在大張旗鼓地進行反恐的同時,“國防轉型”作為一個關鍵詞,也成為國家安全戰略調整的軸心。這種轉型所帶來的后果被人們深切地感受到,卻遲至2003年春美國悍然發動的對伊拉克的戰爭。事實上,這個轉型在此前早就開始了。但是,在中國的國際關系學界里,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由于對以“新保守主義”理念為主導的戰略了解不足,也由于2001年9·11事件所引起的震動,人們對美國反恐戰略背后的國家安全戰略轉型的注意是滯后的。甚至當“Defense Transformation”出現在美國的戰略文獻中時,我們的學界一時對這個概念還找不到適當的中文表達方式,有人使用“國防整改”,也有人翻譯成軍隊“變形”。在含義上也只是把它看作是與“新軍事革命”相同的、一種軍事目標的提法,而沒有把它看作是國家戰略的轉型。也正因為如此,人們對美國究竟要干什么、它的戰略方向和目標究竟是什么,在認識上也滯后于美國的實際行為。
從對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演變軌跡進行的跟蹤、以及對其戰略文獻的梳理考察中,筆者發現“國防轉型”不只是一個軍事領域的概念,實際上集中代表了美國大戰略的改變。而從文獻的追溯中發現,從1997年起“國防轉型”就被提了出來。以Philip A. Odeen為首,以退休將領為主的國防研究小組(National Defense Panel)依據1996年頒布的“軍力結構法案”(Military Force Structure Act)第924節,于1997年向美國國防部提交了一份題為《國防轉型——二十一世紀的國家安全》的研究報告。它當時主要是針對美國的國防戰略提出批評,并提出關于國防轉型的建議。此后,“國防轉型”這個概念被美國的戰略界逐步發展成一個完整的戰略,直至小布什政府的上臺,全面地加以付諸實施。
“國防轉型”(Defense Transformation)反映的不只是為提升美國軍力的主張,而是在戰略理念上拋棄了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接觸戰略,轉變為新保守主義所追求的絕對優勢與絕對安全,其核心是主張以軍事力量作為主要手段,維護美國不可挑戰的霸權地位;面對未來所有可能的威脅,打造一個能戰勝一切對手和可能威脅的軍事力量。與自由主義相比,新保守主義不僅重視美國今天面臨的威脅,更強調未來可能遇到的挑戰,主張要盡可能長期地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必須超前建構具有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國防轉型的出發點從“基于威脅”轉向“基于能力”,強調不以某個威脅為對象、而以能夠戰勝所有對手為目的,來對美國現有的國防力量進行全面改造。按照這個理念,國防轉型的時間長度至少為20年,內容不僅包括陸軍、海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等傳統軍種的轉型,還包括太空軍事力量、信息戰部隊等具有現代意義的軍事力量的轉型;不僅涉及到美國的核戰略、反恐戰略和國土防衛戰略等,還涉及到美國與其盟國的關系及與之相關的美國國內外軍力部署的重組與調整。國防轉型的戰略框架實際上已經超越了國防戰略的范疇,而涉及到了整個美國國家安全戰略。
9·11事件的發生,給小布什政府加快推行國防轉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政治環境。2001年美國國防部所提出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明確提出了國防轉型的計劃。2002年白宮提出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雖然以反恐為主要內容,但它的落腳點卻在于國家安全機構的轉型,其中主要是國防轉型。2005年,美國國防部又將提出新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進一步明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恐怖主義、“失敗國家”和關鍵地區大國的崛起是美國的主要威脅,并強調進一步推進國防轉型。[1]
作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所推行的國防轉型必然會影響到中國的安全環境。從中國的角度來看美國的國防轉型,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
一方面,我們應該看到,美國的國防轉型是以長期稱霸世界為目標、依據美國新保守主義者對后冷戰時期戰略環境的判斷而做出的戰略調整。這個戰略調整的核心是建立美國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不允許在軍事上出現類似美蘇冷戰后期的戰略平衡,也不允許在國際格局中出現新的力量均勢,從而確保美國獨霸世界。因此,美國的國防轉型并不是簡單地、單獨針對中國而作的戰略調整;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對中國的考慮在美國的國防轉型中占有突出的位置。以國防轉型為核心的戰略調整所面對的是一系列“可能的”威脅。除了恐怖主義、“無賴國家”和“失敗國家”之外,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大國挑戰的擔憂也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從近年來美國發布的相關戰略文獻來看,中國已被明確地認定為美國的潛在戰略對手,它的國防轉型中也確實具有明確針對中國挑戰的內容。基于這兩點,我們認為在21世紀前期,美國的國防轉型將對中國的國家安全環境造成如下可能的影響:
從地緣政治層面來看,美國現行戰略所要追求的目標,并不是通過“接觸”讓中國成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一員,而是要阻止中國“控制”東亞這個關鍵地區,其實質就是,美國要繼續主導西太平洋地區的國際秩序,防止中國在該地區、乃至全世界公開挑戰美國。為達到這個目的,冷戰結束以來的長時期里美國一直在低調地構筑著針對中國的“包圍圈”,[2]包括加強在西太平洋的軍事部署、強化與日本的軍事同盟、強化對臺灣問題的干預,以及加強與南亞有關國家的戰略合作。美國以國防轉型為內容的戰略調整,反映出在地緣政治上對中國的政策重心正在從“接觸”向“阻止”、“威懾”和必要時“擊敗”的調整。從這樣的戰略考慮出發,美國為什么千方百計地阻撓歐盟、以色列對中國的武器貿易就不難理解了。
除了國防轉型中直接針對中國的內容外,它還影響著與中國安全環境密切相關的其他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日本和臺灣因素。在這樣的戰略框架下,臺灣問題、日本的意圖都成為可以被用來為美國戰略服務的籌碼。一個針對中國的美國、日本、由分裂勢力主導的臺灣之間或明或暗的合作關系有可能形成。
當然,我們在考察美國的國防轉型對中國安全環境的影響時,還需要注意到中美關系的另外一面。在反恐、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特別是解決朝鮮半島的核問題以及處理伊拉克戰后事宜上,美國的戰略目標是爭取中國的合作。在經濟上,中美之間的相互依賴已到合則雙贏、敗則兩傷的地步。由于美國戰略目標的廣泛性和對立面的多樣性,導致美國在短期內必須處理許多更為急迫的麻煩,而無法把中國作為主要的對手,甚至還需要在一些問題上爭取中國的支持。在這個層面上,多少反映出中美之間在地緣政治和國際關系上還存在著共同利益,使長期的、戰略上的對立被或多或少地淡化或掩蓋。
但是,不可忽視的是,美國的國防轉型在安全上對中國構成了壓力,并使中國對自己的安全環境具有不可控性。這是一個希望實現國家統一、維護國家安全、保持發展勢頭的中國在21世紀初不能不充分重視的。美國以國防轉型為核心的戰略調整對中國的含義在戰略上所帶來的挑戰與機遇,在地理和時間的分布上是不均勻的。
從地理上來看,這種戰略壓力集中于中國的東面,集中于中國的海洋方面,同樣也集中于中國的海上通道和對制海權的競爭上。臺灣的分裂勢力、日本和美國的主要軍事部署都集中在那里。地理上的條件與地緣政治的因素結合成一條島鏈,對中國形成戰略上的包圍態勢。這里既是中國要發展必須要取得的海上安全通道,也是中國面臨的主要安全挑戰。
當然,美國以國防轉型為核心的新戰略自身也有脆弱性,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脆弱性也會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美國的力量可能因此而衰落,國際社會中的力量分布會更均衡,中國可能在戰略上獲得更大的空間。但是,從短期和中期來看,對中國的安全而言面臨的更多的是挑戰。除了美國具有把中國作為潛在戰略對手的意圖之外,還主要由于中美之間實力的高度不對稱、臺灣的分裂勢力具有強烈的追求臺灣獨立的沖動、日本已經出現以中國為戰略對手的傾向。這幾個因素的共同作用、相互關聯決定了對中國國家安全所構成的挑戰十分嚴峻,并且在時間的選擇上,中國并不完全具有主動性,也不是由中國本身的意愿可以決定的。
正是在以上認識的基礎上,我們覺得很有必要系統地研究一下美國的國防轉型究竟包含哪些具體內容,它對中國的現實與長遠含義究竟是什么。2003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批準了對本課題的資助,使我們能夠對這個課題的研究正式啟動。本書正是這項研究的初步成果。這個課題由周建明負責,并撰寫了第一、二、七、十一、十二、十四章和對全書的統稿,王偉男撰寫了第三、四、五、六、十章,并協助對全書的統稿,夏咸軍撰寫了第八章,劉慶榮撰寫了第九章,羅輝撰寫了第十三章。羅峰、胡志勇、夏瑞芳協助翻譯了本項研究所需的部分資料。該課題曾得到國防大學王寶付、徐緯地、華留虎,軍事科學院姚云竹,以及余頑等同志的指正,在此一并表示感謝。由于本課題研究對象的專業性很強,我們的知識結構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時也受到時間上的制約,因此在研究中難免存在錯誤和不準確的地方。如果讀者能予以指正,我們將不勝感謝。
2005年10月